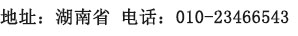夏日纪事:麦粒肿风暴与阳台拔河赛
三明治原创啤桃、澄澄三明治收录于话题#每日书,个
啤桃和澄澄在现实中认识了多年,结为好友余天。在参加了不同月份的每日书之后,她们一起参加了8月共写班。开始写之前,啤桃和澄澄在共写页面上列出了丰富的写作计划,展现出“神仙搭档”的默契(啤桃:奈何理想总是那样丰满)。她们分别写到有关夏天的记忆片段,一个关于麦粒肿,一个关于坏掉的阳台门,从很小的事物切入也可以写出有趣的故事。
文
啤桃、澄澄
编辑
二维酱
啤桃和澄澄,两个切面。
在澄澄眼里,啤桃是用心生活、难免沮丧但勇气与热情持存的人,澄澄是望而却步、在别人的生命体验里获知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几番出入泥淖,越挫越勇,自己则旁观爱的寓言,收获一些相信的可能性。
在啤桃眼里,澄澄是智思、哲学和诗歌,她在书页、电影及一切人类文明的美好里航行,捕捉每一次脑电花的闪光,凝结为隽永的文字。“生活在别处”,澄澄总是从难忘的精神旅途里,兜住困兽之斗的啤桃,给她带来新的光亮。
虽然两个人的生活方式与写作方向都大相径庭,但我们还是努力拾掇出了几个有交集的话题,作为这个月可能会写的内容:
时空观察
Observer
澄澄可能会依托于《马可瓦尔多》(正以每天读个三四页的龟速试图解决它)里打动自己的城市生活细节,模仿朱朱改写故事的笔法,生成一点拙劣的诗歌碎片。
啤桃延续六月书写的笔调,写写小时候的事。我心里好像还是一直住着一只读小学的小啤桃,每次下笔时,都叫嚣着要写写她的事情。盛情难却,我答应了她。
大概也会写写南京,一个我待了太久,太久的城市。
爱LOVE
澄澄澄澄对于“爱”的认知非常非常依赖想象。会被一些话和一些故事打动:
柏拉图的故事里苏格拉底说:爱是丰饶神与匮乏神所生的精灵。
一位诗人也是诗评家布罗茨基的观点是:爱是无限对有限所持的一种态度,而有限对无限所怀揣的态度,则构成了信仰或诗歌。
澄澄觉得,之所以被打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具体的生活形式使话本身不流于空洞,所以也想在谈感想谈心得的过程中,在我的表达能力范畴内,收集一些日常里获得的琐碎关怀。
啤桃是埋在心里,很想写,但还不知如何下笔的故事们。
爱与亲密关系,我一生都要学习,还在学习的主题。
读书
Reading
澄澄
啤桃
澄澄报名每日书的初衷:自己太懒,需要外在机制督促我读书。
啤桃同上,澄澄在报名的最开始就说,我们应该在这上面互相督促读书和写毕业论文。来都来了,那就看看能读多少写多少吧。
心虚.jpg/不立flag
以下内容来自“时空观察”
啤桃:麦粒肿往事
麦粒肿,俗称针眼,是一种发生在睫毛毛囊附近的急性化脓性炎症。一夜的大哭过后,兴许是擦眼泪时胡乱用了手,兴许是前一天学画卧蚕时戳进了睫毛,总之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时,左眼处已经传来了微微的痛感和滞感。心里一沉,我赶紧爬起冲到洗手间检查。唉,没逃过,又是麦粒肿。
每年长一次麦粒肿,不知不觉已经成了我的身体如春去秋来般执行的一条自然规律,一如每半年一次的感冒。在一年天的三百五十天日子里,身体,作为承载着我这位蛮横无理、不知节制的暴君的小船,尽职尽责以薄薄的船板抵御着外界的风浪。我深感它的力不从心,却依然在每次掌舵时,意志软弱地顺从了情绪海怪的歌声,一次次带它驶入最危险幽深的海域。熬夜,痛哭,暴怒,邋遢,我粗暴地对待我的小船,直到它终于撑不下去,只好善意地以亮起红灯的姿态提醒我的暴虐统治。麦粒肿,在观看世界的瞭望镜前凝结为焦灼的火花。
红霉素与热鸡蛋,麦粒肿风暴中,最关键的两个核心意象。第一次长麦粒肿,在小学六年级。那天起床后我就感觉眼睛瘙痒,没在意,照常上了学。午饭后还是难受,赶紧跑去了校医处。校医轻轻扒开我的眼睑,随后拿来一管迷你版牙膏一样的药物,上面写着“红霉素眼膏”。在记账的本子上,我看着她写下我的名字,麦粒肿的名字,红霉素眼膏的名字,以及最后一栏金额上的“0.5元”。我将信将疑地拿走了眼膏,心里满是问号:这么便宜的药,能治病?随之又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我们小学也太穷了……
在午休宿舍里,漂亮的美术老师(兼午休老师)给我涂上了那黄色的黏稠的透明的膏体。我的眼睛被蜂蜜色的浆糊封印,隔着朦胧的复古滤镜,她细长白皙的手指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我安心地闭上了眼睛。短短的一个午觉过后,来势汹汹的麦粒肿竟然就这么奇迹般地消了下去。
这件事让我对校医的态度大为改观,以至于在小学毕业后的很多年里,每当我医院而被开了近百块钱的药物时,我都会真诚地缅怀起那位只用了一根旺旺冰棒钱就将我疗愈的校医。
麦粒肿总发生在夏天,大概是夏季的细菌过于旺盛,而炎热的天气又时常让汗滴混入眼中。记忆里的第二次麦粒肿是暑假,在哥哥家。那时大姨的刚刚搬出老屋,入住独立的新居,我便趁着暑假来寄居一段时间。大概是哥哥从来没长过麦粒肿,大姨一开始着实被我肿起的眼皮吓了一跳。医院当护士,带我去看病,医生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热敷和眼膏来缓解,如果还消不下去,恐怕就只能做手术切除了。我被吓得快哭出来,又怕哭了更加严重,只好眼圈红红地拼命忍住了。回家后,大姨听从医嘱,到厨房里煮鸡蛋给我热敷。哥哥好奇地看着眼睛肿的半睁的我,顺手拿起了药品的说明书。
他边看边念:“不良反应有:过敏导致的发烧、瘙痒、眼睛灼热……”我看到哥哥的脸色越来越差,“严重时可能导致气道阻塞、呼吸困难等”。哥哥啪得一下把说明书拍在桌上,大姨拿着鸡蛋走过来,哥哥忧心忡忡地望望她,又望望我,皱起眉头:“妈,你还是别给我妹滴这个药了。太可怕了!我不同意!”大姨哭笑不得,骂道“呸!说啥不吉利的呢!大吉利是大吉利是!”
在大姨好一番关于不良反应的概率解释过后,哥哥终于迟疑地把眼药水递了过来,眼里依然满是放不下的关切和担忧。其实,从小体弱、吃药长大的我并不担心这张说明单上危言耸听的不良反应,但一想到可以借此要挟他,当时的我还是故作委屈地小声说道:“哥,这些天我不能用眼过多,妈妈要检查的数学作业你可以帮我写写吗?”果然,哥哥摸了摸我的头,拍拍胸脯,从未如此爽快地答应了。
热鸡蛋,“热”属于我,“鸡蛋”属于哥哥。在那个遥远的暑假,乔迁新居的大姨身上背负着每个月几乎占去她百分之八十工资的房贷压力。为了省电,暑假里的许多个夜晚,她都不许我们开灯。哥哥家的阳台正对着那个小县城里最繁华的商场,拉开窗帘,广告牌的灯确实可以照亮大部分客厅。于是,在半明半暗的夜里,大姨、哥哥和我常常就着这点窗外的光亮杀上十几盘五子棋。霓虹灯的光影变幻,棋盘上的白子也因而时红时黄,犹如春节挂在桔子树上跃动的小彩灯。在这样精打细算的生活中,一个鸡蛋的浪费是不被允许的。于是,每天晚上我用毛巾包裹着的鸡蛋热敷完毕后,如何善待这只可怜的食物,便成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大姨不爱吃鸡蛋,我因为发炎不宜吃蛋,最后,这一节约粮食的重任当之无愧地落到了哥哥身上。一开始,哥哥是拒绝的(的确,谁也很难接受自己即将入嘴的食物前一分钟还是别人的按摩工具)。但在大姨极具压迫性的眼神和我哀求的可怜目光里,他还是败下阵来,以一种壮士赴死的决心,在五顿水煮鸡蛋的夜宵代价后,终于换来了他的妹妹再次健康的眼睛。
复诊那天,哥哥也陪着我去了。离开诊室之前,他突然回过头,问了一句:“医生,下次如果再长,可以用鹌鹑蛋热敷吗?”年轻的男医生睁大了双眼,哥哥挠了挠头,咧开嘴笑了,“我觉得……鹌鹑蛋更好吃一点。”
澄澄:阳台纪事
家里阳台落地窗门的滚轮坏了。回回我要进出阳台、推拉那扇门时,都觉得在参与一场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平手的拔河赛。赛事往往开始于这个节点,推至某处,装着门把手的这侧总是莫名翘起,而我使出的平推的力便被这斜度一瞬间导入地下。力转了弯,手上阻塞起来,心里也跟着犯堵。我的一腔怨怒随之被瞬间激出,而又因我的脱力而瞬间消解。我只能一边试图加强力道(以甚至扭到腰为代价),一边提防这点绵薄的蛮力,会不会恰好又作用在哪个不中用的零件上,想象着“咔”一声,整扇门向我倾倒的场面,自觉结局大概不是被门压垮就是被我爸骂垮了。
终于等到这个空闲的上午。在他喊我递一把剪刀时,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往常一样兴致索然地应答一声,只准备充当一副没有感情的人肉传送带。短短两步路里脑子充塞着一团诗的浆糊。然而走到房门前就被惊住,不是被他的伟力——其中一扇门已被横放,倚靠在他的脚和墙间的狭缝处,另一扇门不知所踪——而是被这毫无阻拦的光的力度:在碍眼的暗色门框、玻璃和上面斑驳着的水渍灰尘被从此处移除后,视野从一枚逼仄的取景器扩宽为一副广角镜头,浸润在空气中的一切显得那么鲜活与直接,风滚着天和蓝白的大色块,随着车的川流的音响扑面而来,吹得阔绰。
我不走了。我发出和昌耀卧躺在草场上看到结成灯藤的大熊星座时同样的感慨,一屁股坐在窗边的床上。
风挠着我的脚,我的脚挠它自己。对面大平层上立着的遮阳伞,任风掀起它的下摆的,在半蹲着的爸爸的灰白相间的头发边,跃动得正欢。穿着橙黄色睡裙的留着波浪卷的女人,从边上的铁门走出,站着看了会儿,又转回身去。在爸爸试图和我解释滚轮构造的时刻,那些栖居在轴承中的小圆铁珠,便像被点到名一样兴奋,一颗一颗随之滚落,掉在地上,发出不怎么清脆的声响。而他以他一贯的耐心,把那些因存在时间过久而变得有个性的珠子们小心地拨到一旁,然后知难而退地改选PlanB,叫我起来帮扶着门框,自己去客厅拿润滑油。我虚搭住粗糙的被晒得有些温热的不锈钢边框,延迟地感到夏天的余温朝我慢慢逼近。
白里泛黄的塑料滚轮在油中洗净自身,像裹上一层剔透而耐久性强的光膜。可转动起来还是费力,且咯噔咯噔地响着。“锈掉了里面”,爸爸见我盯着看,又要演示。我连忙制止了他。
上好了油,擦干手。他起身,试图将放倒了的门扭转回直立状,再把它安回槽里。不知道是怕我帮倒忙还是担心我帮不上忙,他也没开口求助,一边解说着“这很重啊”,一边身体力行地用紧绷的肌肉、弯曲受力的背脊,勾勒出这面玻璃的重力。门的顶部在窗槽的周遭虚浮地晃着,丝毫没有要卡进去的意思。他的嗓子挤出一些气音,那些重物压人的画面在我脑中重新闪现。我连忙接过其中一侧,在位置合当之际帮着向上一顶。终于成功。
另一扇门的防灰条半脱落着,邋邋遢遢地垂下一条长尾巴,像根散漫的藤条。我用双臂固定好门,让爸爸踩上小板凳去修剪。只这么抬头一刻,(本是为了确保自己扶稳这个重物的,当时多么害怕手一抖,门的顶部嗑到爸爸的牙,那么铁定吾命休矣了),一片蓝色撞进我的视线,玻璃在偏离了垂直度的站立状态中竟一下变得澄澈,将整片天和街景都搬上版面。好生奇妙,熟视无睹的景,只换了个承载体,就让我有了搬家之感。
在默契中,第二扇门顺利入槽。房间又恢复了原状。
我坐回床头,延迟地察觉一种不舍,记起几日前一个台风天的中午,我大开着窗,在淅淅沥沥声中午睡的感觉。那种介于沉闷和暴烈间的恰切力度可遇不可求,只能企求窗,把所有频段都关在外面。但好奇和贪念诚然关不住,它们会借着某个屋子坏掉的瞬间,或是专制的家长不在场的时刻,溜出来,附着在我自动放弃了思考能力的躯壳上,指挥我制造一些麻烦又无意义的场面。然后再指挥我记下,哪怕看上去断断续续、磕磕巴巴。
原标题:《夏日纪事:麦粒肿风暴与阳台拔河赛
三明治》